《逆天命:元清明》由天涯沦落人001所撰写,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故事,也是一部良心历史脑洞著作,内容不拖泥带水,全篇都是看点,很多人被里面的主角无所吸引,目前逆天命:元清明这本书最新章节第13章,写了124308字,连载。主要讲述了:至正十一年正月廿三,黄泛区边缘的柳林村飘着碎雪。村口老槐树下的草棚里,十二岁的阿禾正用冻裂的手指给妹妹阿荞编草蚂蚱——草是从雪地里扒的,干硬如铁丝,她编断了三次,指尖渗出血珠,染红了草茎。“姐,税吏还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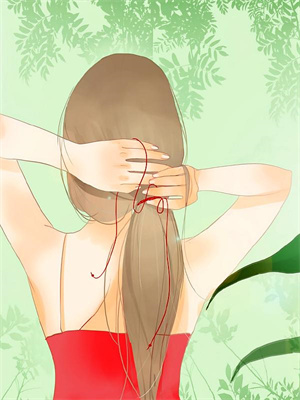
《逆天命:元清明》精彩章节试读
至正十一年正月廿三,黄泛区边缘的柳林村飘着碎雪。村口老槐树下的草棚里,十二岁的阿禾正用冻裂的手指给妹妹阿荞编草蚂蚱——草是从雪地里扒的,干硬如铁丝,她编断了三次,指尖渗出血珠,染红了草茎。
“姐,税吏还来吗?”阿荞的声音像只受惊的雀儿,往阿禾怀里缩了缩。她怀里揣着块观音土饼,是昨日娘用最后一点柴火烧的,饼边已经冻成了硬块,却被她捂得温热。
阿禾把草蚂蚱塞进妹妹手里,摸了摸她枯黄的头发——阿荞去年还长着黑亮的头发,自从黄河溃口、爹被抓去修堤后,她就天天啃观音土,头发渐渐褪成了枯草色。“不来了。”阿禾说谎时,眼睛盯着村口的路,路尽头的雪地上,已经出现了几个小黑点。
那是河南税吏王德才带着兵丁来了。上个月他来催收“河工捐”,说每户流民要交三斗米,交不出就“以人抵税”——当时抓走了村西头李家的二小子,说要送去大都给密宗僧侣当“侍童”,至今没回来。
“阿禾姐!税吏来了!”村口放哨的狗剩跑过来,棉裤的裤脚用草绳绑着,露出的脚踝冻得发紫,“我看见王税吏的算盘了,还听见兵丁说‘今天要抓够十个娃’!”
草棚里的流民瞬间慌了。有个老婆婆把孙子往草堆里塞,用破棉袄盖住;有个汉子攥紧了手里的木棍,指节发白;阿禾的娘陈氏突然站起来,把阿荞往阿禾身后推,自己往草棚外走——她想往村后的芦苇荡跑,那里有个地窖,是上个月藏观音土用的。
“想跑?”王德才的声音在村口炸响,他穿着件半旧的锦袍,腰间挂着把铜算盘,算珠被磨得发亮。身后跟着四个兵丁,手里的刀在雪光里闪着冷光,刀鞘上还沾着去年的血渍。
陈氏刚跑出草棚,就被兵丁一脚踹倒在雪地里。她怀里的观音土饼滚出来,摔成了碎块,混着雪粒散了一地。“王税吏,我们交!我们交!”她趴在地上磕头,额头撞在冻硬的地上,发出闷响,“我去给大户人家做佣人,我去挖煤窑,别抓我的娃!”
王德才蹲下来,用靴尖挑着她的下巴,算盘在手里打得噼啪响:“陈氏,你男人赵老实欠河工捐三斗米,滞纳金两斗,上个月的人头税一斗,合计六斗——你觉得你去挖煤窑,能值六斗米?”
他的算盘珠停在“六”上,铜珠冰凉。阿禾记得爹临走时说,修堤的监工把石料换成了沙土,还克扣粮饷,爹就是因为偷了半块干粮,被监工打死在堤上的——可税吏不管这些,他们只认账本上的数字。
“我……我有件棉袄。”陈氏从怀里掏出个布包,里面是件打满补丁的棉袄,领口还绣着朵歪歪扭扭的梅花——是阿禾出生时,她用嫁妆布缝的,“这是细棉布的,能当半斗米。”
王德才接过棉袄,往地上一扔,用靴底踩得稀烂:“去年还能当半斗,今年?连喂狗都嫌硬。”他站起来,目光扫过草棚,像鹰在找猎物,“要么交米,要么交人——十岁以下的娃,女娃一个抵两斗,男娃一个抵三斗,你们自己选。”
草棚里的空气瞬间冻住了。有个妇人突然尖叫起来,死死抱住怀里的孩子:“我的娃才五岁!你们是畜生吗?”兵丁冲过去,一把扯开她的胳膊,孩子吓得大哭,哭声像刀子割在每个人心上。
“张婶!”阿禾突然把阿荞往草堆深处塞,自己冲出去挡在那妇人身前,“别抓她的娃!抓我!我十五了,能抵三斗米!”
王德才上下打量着她,算盘又响了:“十五?过了值钱的年纪。不过瞧着结实,能给军爷当使唤丫头——算你抵两斗,还差四斗。”
“我也去!”狗剩从草堆里钻出来,手里还攥着块石头,“我是男娃,能抵三斗!”
“狗剩!”阿禾想拦他,却被兵丁按住了肩膀。狗剩的爹娘去年死在黄河里,他跟着阿禾一家过活,比亲弟弟还亲。
“还差一斗。”王德才的算盘打得更响了,珠子碰撞的声音在雪地里格外刺耳。他的目光落在草堆里——阿荞的破棉袄角露在了外面,像朵苍白的花。
陈氏突然扑过去,用身体挡住草堆:“不准动我的小女儿!她才七岁,她还在咳嗽!”她的声音嘶哑,嘴角渗出血丝——刚才磕头时磕破了嘴。
王德才笑了,算盘往腰间一挂,亲自走过去扒开陈氏的手。阿荞缩在草堆里,抱着草蚂蚱发抖,小脸冻得发紫,却死死咬着嘴唇不吭声。“这女娃长得俊,送进国师府当侍童,说不定能值四斗。”他抓住阿荞的胳膊,就往外拖。
“放开我妹妹!”阿禾挣脱兵丁,扑过去咬住王德才的手腕。牙齿嵌进他的皮肉,尝到了咸腥的血味——这是她第一次咬人,像被逼到绝境的小兽。
“反了!”王德才疼得大叫,另一只手抽出腰间的短棍,狠狠砸在阿禾背上。阿禾被打得趴在地上,背上火辣辣地疼,却还是盯着妹妹:“阿荞!往芦苇荡跑!找李大叔!”
阿荞哭着摇头,小手死死抓住阿禾的衣角:“姐不走,我也不走!”
兵丁把阿禾拖开,用绳子绑住她的手腕。王德才捂着流血的手腕,一脚踹在阿禾脸上:“小贱人!等把你卖到煤窑,看你还敢咬人!”他指了指阿荞,“这两个,还有那个男娃,都带走——刚好抵六斗米,再多赚一斗!”
陈氏看着被兵丁拖走的三个孩子,突然瘫坐在雪地里,抓起地上的观音土往嘴里塞,嚼得嘴角冒白沫:“我也交!我也抵税!把我也带走!”可没人理她,兵丁押着三个孩子已经走出了村口。
阿禾回头时,看见娘还坐在雪地里,像尊没有知觉的石像,身边散落着碎成渣的观音土饼。狗剩被兵丁推搡着,却还回头对她喊:“阿禾姐!我记住王税吏的样子了!等我跑了,就去告他!”
兵丁给了他一棍,骂道:“小杂种还想跑?到了大都,把你卖给喇嘛当祭品!”
队伍往县城走时,又进了两个村子,抓了七个孩子,刚好凑够十个。兵丁用绳子把孩子们串起来,像串牲口,走得慢了就用鞭子抽。阿禾走在最前面,手腕被绳子勒得生疼,却还是尽量挡住后面的阿荞——她怕妹妹被鞭子抽到。
路过黄河故道时,孩子们看见冻在冰里的尸首,有个小男娃吓得哭起来,被王德才用算盘砸了脑袋:“哭什么?再哭把你扔进去喂鱼!”那尸首穿着破烂的河工服,阿禾认出那是爹同村的李大叔——上个月还说要帮她们找地窖。
“姐,我冷。”阿荞的声音带着哭腔,小脸蛋冻得像个红苹果。阿禾把妹妹的手揣进自己怀里,那里还有点温度。她想起娘绣的梅花棉袄,想起草蚂蚱,想起地窖里的观音土——原来她们拥有的,只有这些随时会被夺走的东西。
快到县城时,路边出现个茶棚,棚下坐着个穿青布衫的老秀才,正用炭笔在纸上写着什么。他看见被绑的孩子,突然站起来,拦住了队伍:“王税吏,朝廷有令,不准掳掠流民子女!”
王德才认出他是前几年罢官的县学教谕周先生,冷笑一声:“周老秀才,你都自身难保了,还管别人?上个月你替流民写状子,被县太爷打了三十大板,忘了?”
周先生的背还驼着,是被板子打坏的,可他还是挺直了腰:“我是秀才,读的是孔孟之道,见不得你们如此禽兽行径!”他把手里的纸往王德才面前递,“这是《流民血泪状》,我已经抄了十份,要往大都递!”
王德才抢过状子,撕成碎片:“递?你能递到哪?上个月有个御史递奏章,被我们大人折成了酒器垫!”他用算盘指着周先生,“再挡路,连你一起抓去抵税——老东西,说不定能值半斗米!”
兵丁推开周先生,押着孩子往前走。阿禾回头时,看见老秀才蹲在地上,一片一片捡着碎纸,手指冻得通红,却还在念叨:“我记着呢……王德才,河南归德府税吏,至正十一年正月廿三,掳掠流民子女十名……我都记着呢……”
县城的牢房阴暗潮湿,十个孩子被关在一间空牢房里,墙角堆着些发霉的稻草。阿荞缩在阿禾怀里,小声哭着,狗剩则在牢房里转圈,打量着墙壁:“这墙是土坯的,晚上咱们挖个洞跑!”
阿禾摸了摸墙壁,土坯冻得像石头,根本挖不动。她从怀里掏出个东西,是块小小的木牌——是爹修堤前给她的,上面刻着个“安”字,说能保平安。“拿着这个。”她把木牌塞给阿荞,“要是分开了,就带着它,姐能找到你。”
傍晚时,王德才带着个穿绸衫的男人进来,那男人是“人牙子”,专门给大都的贵族和密宗寺院找童男童女。他挨个打量孩子,像在挑牲口,手指捏捏这个的脸,摸摸那个的胳膊。
“这个女娃不错,皮肤白。”人牙子指着阿荞,“给国师府的喇嘛送去,能换五斗米。”他又指了指阿禾,“这个结实,给煤窑老板,能换三斗。”最后指了指狗剩,“这男娃眼神凶,给西域来的商人当侍从,能换四斗。”
王德才的算盘打得噼啪响:“五加三加四,十二斗——扣除本钱六斗,净赚六斗!好!”他对人牙子说,“今晚就装车,明早出发,别让县里的官差看见。”
人牙子走后,王德才给孩子们扔了些发霉的窝头,就锁上了牢门。阿禾把窝头掰成小块,先给阿荞和最小的孩子,自己只吃了点碎屑。“今晚别睡太死。”她对狗剩说,“他们要装车,说不定有机会跑。”
深夜时,兵丁果然来提人。孩子们被蒙上眼睛,塞进辆闷罐车。阿禾和阿荞被分开了,她能听见妹妹在隔壁车厢哭,却喊不出声——嘴里被塞了破布。
马车走了不知多久,颠簸得厉害。阿禾在黑暗中数着时间,听着车轮的声音——她小时候跟着爹赶过车,知道车轮压过石板路和土路的声音不一样。当她听见车轮碾过沙子的声音时,知道快到黄河渡口了——那里有片芦苇荡,爹说过,芦苇荡里藏着水鸟,也藏着活路。
她开始用被绑的手腕蹭车厢壁——那里有块松动的木板,是她刚才摸出来的。蹭了不知多久,手腕被磨出血,木板终于被蹭开个缝。冷风灌进来,带着芦苇的气息。
“狗剩?”她对着缝隙小声喊,“在吗?”
“在!”狗剩的声音从前面传来,“我也在摸木板!”
“等下过了渡口,车要上渡船,那时兵丁会松绑让我们下车——咱们往芦苇荡跑!”阿禾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发颤。
没过多久,马车停了。兵丁打开车门,把孩子们拉下来,解开绳子让他们上渡船。阿禾被推搡着往前走,眼睛还被蒙着,却能听见黄河的水声,能闻到芦苇的味道。
“就是现在!”她突然喊了一声,猛地扯掉眼上的布,拉起身边一个小女娃就往芦苇荡跑。
“跑啊!”狗剩也反应过来,拉起另一个孩子冲进芦苇丛。
兵丁愣住了,等反应过来时,三个孩子已经钻进了芦苇荡,只能看见晃动的芦苇杆。“追!”王德才气得大叫,带着两个兵丁追了进去。
芦苇比人还高,雪地里的脚印很快就乱了。阿禾拉着小女娃在芦苇丛里钻,脚下的淤泥深一脚浅一脚,冰冷的水灌进鞋里,冻得脚趾发麻。“别怕,跟着我。”她对怀里的孩子说,声音却在发抖——她也怕,可她知道不能停。
身后传来王德才的咒骂声,还有兵丁的刀砍芦苇的声音。阿禾突然想起爹教她的:“迷路了就看星星,北极星永远在北边。”她抬头,看见芦苇缝隙里的星星,辨了辨方向,往西北跑——那里离柳林村最近。
跑了不知多久,身后的声音渐渐远了。阿禾把孩子藏在一丛茂密的芦苇里,用破棉袄盖住她:“你在这等着,我去看看有没有人追来。”
她刚走出去几步,就看见王德才拿着刀站在前面,脸上全是泥,像头暴怒的野兽。“小贱人!我看你往哪跑!”
阿禾转身想跑,却被他抓住了头发,狠狠往地上拽。她的头撞在冻土上,眼前发黑,却还是抓起身边的石块,用尽全身力气砸向王德才的脸。
“啊!”王德才惨叫一声,松开了手。阿禾看见他的额头流血了,顺着脸颊往下淌,像条红色的蛇。
她趁机爬起来,往芦苇深处跑。王德才捂着额头追,嘴里骂着:“我要杀了你!把你剁成块喂狗!”
就在这时,芦苇丛里突然冲出几个黑影,手里拿着木棍和鱼叉,为首的是个络腮胡汉子——是柳林村的李大叔,他藏在芦苇荡里打野鸭,听见动静就赶过来了。
“王税吏!你还敢追!”李大叔一叉叉在王德才腿上,疼得他倒在地上,“上个月你抓我儿子,这个月又抓阿禾!我看你是活够了!”
几个汉子围上来,拳打脚踢。王德才的算盘掉在泥里,算珠滚得满地都是,像他那些算不清的黑心账。
阿禾找到藏起来的小女娃,又跟着李大叔在芦苇丛里找,找到了狗剩和另外两个孩子,却没找到阿荞。“阿荞呢?”阿禾的声音发颤。
狗剩低下头,眼泪掉下来:“刚才乱跑,我跟她走散了……我听见她喊‘姐’,可芦苇太深,我找不到……”
李大叔拍了拍阿禾的肩膀:“别急,我们分着找。王税吏说要把孩子卖到大都,阿荞肯定没走远——说不定被路过的流民救了。”
他们在芦苇荡里找了一夜,天亮时也没找到阿荞。李大叔把被救的四个孩子藏在地窖里,那里有他们藏的红薯和干柴。“你们先在这待着,我出去打听消息。”他临走时塞给阿禾一把小刀,“要是有人来,就用这个防身。”
地窖里,阿禾摸着怀里的木牌,上面的“安”字被汗水浸得发亮。她想起妹妹的草蚂蚱,想起娘散落的观音土饼,突然拿起小刀,在窖壁上刻了个“税”字——刻得很深,像要嵌进石头里。
“我记住了。”她对自己说,也对窖壁上的字说,“王德才,河南税吏,用流民子女抵租税。我阿禾,柳林村人,我记着呢。”
三天后,李大叔回来了,带来个消息:阿荞被路过的红巾教徒救了,现在在淮西的根据地,那里管饭,还教孩子认字。“红巾教的人说,等开春就打回来,杀贪官,分粮食,再也不让税吏抓孩子。”
阿禾摸着窖壁上的“税”字,突然笑了,眼里却掉出泪来。她想起老秀才捡碎纸的样子,想起李大叔的鱼叉,想起红巾教徒——原来这世道,还有人在记着这些事,还有人在想着救他们。
她把小刀递给狗剩:“你看,这字刻得够深吗?等我们出去了,就把它刻在村口的老槐树上,让所有人都看见。”
狗剩接过刀,在“税”字旁边刻了个“恨”字:“再刻个恨!让王税吏看见,吓破他的胆!”
地窖外的雪还没化,可阳光已经能透过芦苇照进来,在雪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李大叔说,黄河的冰开始化了,等冰化了,就能坐船去淮西,去找阿荞,去找红巾教。
阿禾摸着怀里的木牌,仿佛能听见妹妹在喊“姐”。她知道,不管要走多远的路,不管要过多少条河,她都要找到妹妹——因为她们是被这世道逼到绝境的野草,却也像野草一样,只要有一点阳光,就能扎下根,就能等着春天。
而那个刻在窖壁上的“税”字,会像颗种子,在所有被掠夺、被伤害的人心里发芽,长成能掀翻这黑暗的力量。就像红巾教徒说的:“只要还有人记得恨,就有人敢反抗。”
小说《逆天命:元清明》试读结束!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