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我在异常收容部队服役的那些年》是一本引人入胜的都市高武小说,作者“水咕咕爱学习”以其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描绘,为读者们展现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世界。本书的主角陈骁深受读者们的喜爱。目前这本小说已经更新至第15章,总字数210548字,热爱阅读的你,快来加入这场精彩的阅读盛宴吧!主要讲述了:那辆黑色的轿车,就像个没有生命的铁皮棺材,载着我在高速公路上闷头狂奔。整整一天一夜,我感觉自己的屁股都要颠成八瓣了。这期间,司机换了两个,都是那种沉默寡言、面无表情的汉子,开车稳得像机器人。唯一不变的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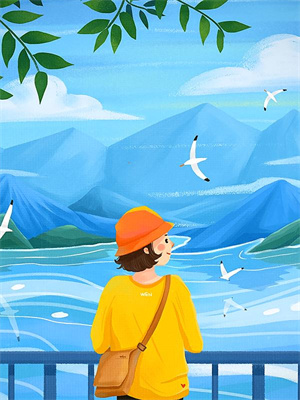
《我在异常收容部队服役的那些年》精彩章节试读
那辆黑色的轿车,就像个没有生命的铁皮棺材,载着我在高速公路上闷头狂奔。整整一天一夜,我感觉自己的屁股都要颠成八瓣了。这期间,司机换了两个,都是那种沉默寡言、面无表情的汉子,开车稳得像机器人。唯一不变的,是坐在副驾驶上的那个自称老K的男人。
他从上车开始,就跟入定了一样,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,连姿势都没怎么换过。我好几次想找点话说,比如问问“大哥,咱们这是去哪儿啊?”或者“这车不错啊,得不少钱吧?”,但每次话到嘴边,看着他那张跟冰雕似的侧脸,我又给咽了回去。纪律,他之前提过。我签了那份文件,就不再是那个可以随便插科打诨的保安陈野了。现在,我是国家的兵,虽然是个代号叫【疯子】的兵。
车窗外的景色,像是一部快进的电影。一开始还是高楼林立,灯红酒绿,充满了人间烟火气。我甚至看到了一家我以前经常去吃宵夜的烧烤摊,老板正忙着给烤串刷油,那熟悉的孜然味儿仿佛穿透了车窗,钻进了我的鼻子。我心里咯噔一下,有点发酸。那便是我的过去,一个虽然平凡但至少安稳的世界。而我,正坐在一辆没有牌照的车里,朝着一个完全未知的方向,一去不回头。
渐渐地,城市的灯火越来越稀疏,最后彻底消失在地平线上。取而代之的,是连绵不绝的黑色山脉,像一头头趴在地上的远古巨兽,在月光下露出狰狞的轮廓。再往后,连山都看不见了,只剩下无边无际的荒漠,除了单调的黄色,什么都没有。车里安静得只剩下轮胎压过路面的“嘶嘶”声,这种极致的单调和寂静,比城市的喧嚣更让人心慌。
我不知道过了多久,可能又是一个白天。车里的空调开得很足,但我感觉不到一丝暖意。老K始终没动,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睡着了。中途换司机的时候,是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地里。另一辆一模一样的黑色轿车悄无声息地滑到我们旁边,车上下来一个同样面无表情的司机,和我们车里的那个交换了一下眼神,点了点头,然后就完成了交接。整个过程不到三十秒,没有一句话,配合得天衣无缝。我看着那个离开的司机上了另一辆车,很快就消失在烟尘里,感觉自己像是在看一部间谍片。
终于,我们的车子也慢了下来,离开了平坦的公路,一头拐进了一条根本不像路的路。与其说是路,不如说是在戈壁滩上被车轮硬生生压出来的两条辙。车子开始剧烈地颠簸起来,我的五脏六腑都感觉错了位。窗外的景象,也变得越来越诡异。风蚀过的土丘奇形怪状,有的像蘑菇,有的像城堡,有的像扭曲的人脸。这里绝对是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,是真正的生命禁区。我敢打赌,把一个活人扔在这儿,不出三天,不是渴死就是被太阳晒成了人干。
又在这种鬼路上颠了几个小时,颠得我快把隔夜饭都吐出来了,车子总算在一片巨大的雅丹地貌前停了下来。这里给人的感觉,就像是地球的疤痕,荒凉、死寂,充满了末日感。放眼望去,除了漫天黄沙和那些被风啃得奇形怪状的土丘,连根草都看不见。
“下车。”老K的声音突然响起,像是生锈的铁门被拉开,嘶哑又干涩。这是他这一天一夜里,对我说的第一句话。
我和他推门下车,一股热浪夹杂着沙土的气味扑面而来,呛得我咳嗽了两声。另一个司机二话不说,立刻调转车头,油门一踩,就像后面有鬼追一样,头也不回地沿着来路狂奔而去,仿佛一秒钟都不想在这里多待。
空旷的戈壁上,只剩下我和老K两个人,还有我们孤零零的影子。那种被世界抛弃的感觉,强烈得让人窒息。
老K没理会我的不适,自顾自地带着我,走到一处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土丘前面。这土丘跟周围的上百个土丘没什么两样,扔在人堆里绝对找不出来。他从怀里摸出一个黑色的、有点像老式电视遥控器的东西,对着土丘按了一下。
没有电影里那种惊天动地的巨响,只有一阵低沉的、仿佛大地在呻吟的轰鸣声。我们面前的地面,那片坚实的、被太阳晒得龟裂的土地,竟然从中间缓缓裂开了一道缝。缝隙越变越大,露出一个黑漆漆的洞口,洞口是一个向下延伸的巨大斜坡,坡道是金属材质的,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幽冷的光。一股复杂的味道从地底深处涌了上来,那味道很难形容,像是修车厂里浓重的机油味,混合着医院里刺鼻的消毒水味,还夹杂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、仿佛是把一座尘封了千年的古墓突然打开时冒出来的那种陈腐气息。
“欢迎来到‘归墟’。”老K转过头,面无表情地对我说了这么一句。他的语气里没有丝毫欢迎的意思,更像是在陈述一个冷冰冰的事实。说完,他便率先迈步,顺着那个金属斜坡走了下去。
我犹豫了一下,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那片广袤无垠的荒漠。太阳正要落下,把整个天空烧成了诡异的血红色。我知道,一旦我走下去,可能就再也看不到这样的景色了。我深吸了一口带着沙土味的空气,像是要把这人间最后的味道记在肺里,然后一咬牙,跟在了老K身后。
我能感觉到,我每往下走一步,头顶上那道裂开的缝隙就合拢一分。光线一点点被吞噬,周围的温度也越来越低。当最后一片血色的天空被彻底隔绝,伴随着“咔哒”一声轻响,整个世界陷入了纯粹的黑暗和死寂。那一刻,我感觉自己不是走进了一个地下基地,而是被活埋进了一座精心打造的巨大坟墓。
这里,就是那个“秦陆人民军异常收容部队”的总部基地。
老K不知道按了哪里,通道两旁的墙壁上,亮起了一排昏黄的壁灯。光线很暗,勉强能照亮我们脚下的路。我这才看清,我们正走在一条极其漫长的走廊里。这条走廊根本不是现代建筑的风格,两边的墙壁是用一块块巨大的、表面粗糙的青石条砌成的,石缝之间严丝合缝,透着一股冰冷和压抑。脚下踩的也是青石板,每走一步,鞋底和石板摩擦的声音,都会被无限放大,然后在这空旷的走廊里产生悠长的回音。
头顶上,每隔很长一段距离才有一盏壁灯,光线昏暗得像是快要熄灭的蜡烛,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,在墙壁上像鬼影一样晃动。长廊的两侧,是一扇扇厚重得夸张的青铜大门。门上没有门牌号,也没有任何现代标识,只雕刻着一些我完全看不懂的古老符号,那些符号歪歪扭扭,有的像纠缠在一起的虫子,有的像破碎的星辰,还有的像一只正在流泪的眼睛,看得久了,会让人心里发毛。
整个基地里安静得可怕,除了我们两个人的脚步声,我听不到任何其他声音。没有机器运转的嗡嗡声,没有人员走动的嘈杂声,什么都没有。这种寂静,比任何噪音都更让人感到不安。
偶尔,会有一扇青铜门悄无声息地打开,从里面走出一两个穿着黑色作战服的士兵。他们每个人都身形彪悍,走路悄无声息,像是幽灵一样。但最让人心悸的,是他们的眼神。那是一种空洞的、没有任何情绪的眼神,就像是两颗失去光泽的玻璃珠。他们从我们身边走过,甚至连眼角的余光都不会分给我们一秒,仿佛我们只是两团空气。他们身上散发出的,是一种混杂着血腥味和疲惫感的死气。
我看着他们消失在长廊的拐角,心里忍不住打了个寒颤。这地方到底是怎么回事?这些人又是怎么了?
“为什么……这里要建成这样?这么……复古?”我终于还是没忍住,压低了声音问老K。在这种地方,我连大声说话的勇气都没有。
“为了‘镇压’。”老K的声音在空旷的长廊里回荡,显得格外清晰和阴冷,“我们收容的东西,很多都对环境极其敏感。现代化的、明亮开阔的环境,对它们来说就像兴奋剂。而这种深埋地底、如同陵墓一样的结构,本身就是一种物理和心理上的‘封印’。在这里待久了,你自己都会觉得自己已经是个死人了,那些‘东西’,自然也就安分多了。”
他的话让我后背一阵发凉。把自己当成死人?这他妈是什么鬼理论?可看着那些路过士兵的眼神,我又觉得老K说得或许没错。这个地方,真的会把活人变成死人。
我们大概走了半个多小时,感觉像是走了一个世纪那么长。这条走廊仿佛没有尽头。最后,老K在一扇看起来和别的门没什么区别的青铜门前停了下来,他没有用钥匙,只是用手在门上一个不起眼的符号上按了一下,门就“吱呀”一声,沉重地向里打开了。
“这是你的宿舍,单间。以后你就住在这里。”他侧过身,指了指里面,“记住,除了任务和训练,不要随便串门,更不要手贱,试图去打开别人的房门。这是为了你好,也是为了大家好。”
我探头往里看了一眼,心又凉了半截。房间不大,也就七八个平方。里面空空荡荡,只有一张床,一张桌子,一把椅子,还有一个小柜子。所有的家具都是用最粗糙的金属焊接而成的,边角锋利,闪着冰冷的光。墙壁和地面,也都是和外面走廊一样的青石。这他妈哪是宿舍,这分明就是一间牢房,而且是那种关押重刑犯的单人牢房。
“明天早上六点整,会有人来带你去训练场。别迟到,这里没有闹钟,也没有人会叫你第二次。”老K说完,也不管我有什么反应,转身就走,他高大的身影很快就融入了长廊深处的黑暗里,只剩下我一个人,面对着这间冰冷的石室。
我走进房间,身后的青铜门自动、缓慢地关上了,最后“哐当”一声巨响,彻底隔绝了我和外面的世界。
那一夜,我根本没睡。不是不想睡,是真的睡不着。我躺在那张比石头还硬的金属床上,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。这里没有窗户,分不清白天黑夜,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笼罩着一切。周围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和血液流动的声音。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世界遗忘的囚徒,被埋葬在了这地底几千米深处的坟墓里。我拿出那张金属身份卡,在黑暗中反复摩挲着上面的字。陈野。异常收容部队。【疯子】。我当时还觉得这个代号有点好笑,现在看来,简直是再贴切不过了。能待在这种鬼地方不疯的,那才是真的疯子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,我感觉时间差不多了,就猛地坐了起来。常年当保安养成的生物钟还是有点用的。我摸黑穿好衣服,走到门口,像个傻子一样笔直地站着,等着那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人。
果然,在我估计的六点钟左右,门外传来了一阵轻微的脚步声,然后我面前的青铜门无声地滑开了。门口站着一个男人,身材极其魁梧,像一头熊。他穿着黑色的作战服,脸上有一道从左边眉骨一直延伸到右边嘴角的刀疤,让他的脸看起来格外狰狞。他一句话都没说,只是用那双冷得像冰的眼睛瞥了我一眼,然后用下巴朝外面点了点,示意我跟上。
我不敢怠慢,赶紧跟了出去。
他带着我穿过了几条和昨天差不多的、同样压抑的走廊,最后来到一个巨大的圆形石厅。这个石厅非常大,至少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宽,穹顶很高,上面雕刻着一些看不懂的壁画,因为光线太暗,也看不真切。石厅里已经站了几十个人,看样子都是和我一样的新兵。大家穿着统一的黑色训练服,一个个脸上都带着紧张、茫然,还有一丝掩饰不住的恐惧。
所有人都很安静,没有人交头接耳,整个石厅里弥漫着一股凝重压抑的气氛。
在石厅的正中央,站着一个男人。
他穿着一身笔挺的黑色教官服,戴着军帽,帽檐压得很低,看不清他的长相。他的身材不算特别高大,甚至有些精瘦,但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,就好像一根烧红的钢钉,死死地钉在了地上,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让人心惊肉跳的危险气息。那不是靠肌肉和体型撑起来的压迫感,而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、经历过无数次生死搏杀后沉淀下来的杀气。
所有新兵的目光,都不由自主地集中在他身上。
他等所有人都到齐了,才缓缓抬起头。我这才看清他的脸,很普通的一张脸,但那双眼睛,却像两个黑洞,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情感波动,只有一片死寂。
“我的代号叫阎王,是你们的新兵总教官。”他的声音不大,甚至有些沙哑,但却像无数根冰冷的针,清晰地扎进每个人的耳朵里,“我不管你们以前在哪个部队是尖子,是兵王,还是什么狗屁精英。到了这里,你们以前的所有荣誉,都是一堆垃圾。在我眼里,你们现在,全都是废物!”
他的话音刚落,队伍里有几个人明显身体一僵,眼神里流露出一丝不服气。我也是老兵出身,虽然只是个普通的边防兵,但这种话听着确实刺耳。
阎王似乎察觉到了这些人的情绪,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:“怎么?不服气?很好。我会用事实告诉你们,你们到底有多废。你们的第一个训练科目,叫‘观渊’。意思是,凝视深渊。”
他指了指石厅正中央,那里有一个被厚重的防弹玻璃罩住的巨大金属台。随着他的话音落下,周围的灯光忽然暗了下来,只有一束强光打在那个金属台上。只听见一阵轻微的机械声,金属台上面的盖子缓缓向上升起,露出了里面的东西。
当我看清那东西的一瞬间,我感觉我的大脑像是被谁狠狠地打了一拳。
那是一个……我完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东西。
它的大体轮廓,像是一个黑色的方块,大概有一台老式电视机那么大。但它的每一个面,每一条棱,每一只角,都在以一种完全违背几何学常识和物理定律的方式,疯狂地扭曲、折叠、向内塌陷,同时又向外无限延伸。你盯着它看,会感觉自己的视觉逻辑被彻底粉碎了。它明明是个三维物体,却让你感觉它同时存在于四维、五维甚至更高的维度。你的眼睛告诉大脑“这是一个方块”,但大脑处理完信息后却得出一个结论:“这不是方块,这是不可能存在的悖论”。这种视觉和认知的剧烈冲突,瞬间就引发了强烈的生理不适。
“凝’视它。”阎王的声音再次响起,冰冷得不带一丝感情,“不准闭眼,不准移开视线,不准交头接耳。谁吐了,谁倒下了,谁疯了,谁就给我滚蛋。我们这里,不收留真正的疯子,只收留能驾驭疯狂的疯子。”
我咬紧牙关,强迫自己把视线死死地钉在那个“方块”上。
只看了不到十秒钟,我就感觉胃里一阵翻江倒海,一股酸水直冲喉咙。脑袋里像是被塞进了一个高速运转的搅拌机,嗡嗡作响,剧痛无比。我看到的世界开始扭曲,石厅的墙壁像波浪一样起伏,地面也变得像沼泽一样柔软。
“呕……”我旁边的一个新兵已经撑不住了,他弯下腰,跪在地上剧烈地干呕起来,但什么也吐不出来。
紧接着,另一个新兵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,他抱着自己的头,痛苦地在地上打滚,嘴里胡言乱语地喊着:“别过来!别过来!滚开!”
很快,就有两个穿着白色全封闭防护服、看不清脸的医护人员冲了进来,他们动作麻利地给那个惨叫的家伙打了一针,然后像拖一条死狗一样,把他拖出了石厅。整个过程快得惊人,而且没有发出一点多余的声音。
越来越多的人倒下。有的直接昏死过去,有的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,还有一个甚至开始疯狂地撕扯自己的衣服和皮肤。医护人员像幽灵一样穿梭在人群中,把这些“不合格”的废物一个个清理出去。
我感觉自己的意识也正在被那团疯狂的几何体一点点吸进去,我的理智,我过去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对世界的所有认知,都在以极快的速度瓦解。不行,我不能倒下!我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,我不能就这么像条丧家之犬一样被拖出去!我的人生分界线才刚刚划下,我不能让它成为我的终点线!
我猛地一咬舌尖,剧烈的疼痛让我瞬间清醒了一点。我开始强迫自己不去“理解”它,不去分析它的结构,不去思考它为什么会这样。我开始动用我以前在部队里学到的本事,进行潜伏伪装训练的时候,教官教过我们,如何在一个地方趴上一天一夜而不被发现,诀窍就是放空大脑,把自己当成一块石头,一棵草,把周围的一切都当成没有意义的背景板。
我开始回忆,拼命地回忆。回忆我在雪域高原上每一次巡逻的场景,回忆那里的风有多冷,那里的雪有多白,回忆那种天地间只剩下我一个人的、极致的寂静。我甚至开始在脑子里默写我以前当保安时,小区里那一百多个业主的车牌号。
渐渐地,那种撕裂大脑的感觉,竟然真的减轻了。我发现,当我不再试图用我那可怜的、凡人的逻辑去分析它时,它对我精神的冲击就变小了。它依然在那里疯狂地扭曲,但我只是“看”着它,而不去“思考”它。
我就像一个看着屏幕上无意义的雪花点的观众,慢慢地,我甚至……开始能看清它扭曲的轨迹了。在那些疯狂的、毫无逻辑的线条中,我好像找到了一丝若有若-无的、转瞬即逝的规律。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韵律,就像一首用噪音谱写的、只属于疯子的乐曲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,也许是十分钟,也许是一个小时,阎王那冰冷的声音再次响起:“时间到。”
随着他一声令下,金属台上的盖子缓缓落下,重新罩住了那个黑色的方块。石厅里的灯光也恢复了正常。
我猛地回过神来,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,浑身都被冷汗浸透了,整个人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,双腿发软,几乎站不稳。我环顾四周,这才惊恐地发现,原本几十人的石厅里,还站着的,包括我在内,竟然只剩下不到十个人。
剩下的几个人,也都跟我一样,脸色惨白如纸,眼神涣散,一副丢了半条命的样子。
阎王迈着步子,缓缓地从我们这些幸存者面前走过,他那双毫无感情的眼睛,像X光一样,在我们每个人脸上扫了一圈。最后,他停在了我的面前。
“你叫陈野?”
“是,教官!”我猛地一个立正,用尽全身力气吼了出来。
“感觉怎么样?”他盯着我的眼睛问。
“报告教官,头晕,恶心,想吐,感觉脑子成了一锅粥!”我实话实说,这种时候,没必要装英雄好汉。
“还能站着,还能条理清晰地回答我的问题,就算不错了。”阎王居然点了点头,脸上看不出是喜是怒,“你比我想象的,要能扛一点。不过,别高兴得太早,这只是开胃菜。连正餐前的漱口水都算不上。”
说完,他冲我一摆头:“走,跟我来。”
我愣了一下,看了一眼身边剩下的那几个同样一脸懵逼的战友。他竟然要单独把我带离队伍。
我不敢多问,立刻跟了上去。他带着我,没有回到我们来时的路,而是走向了石厅另一侧的一条更深、更黑暗的通道。这条通道比之前那条还要压抑,墙壁不再是青石,而是某种黑色的金属,摸上去冰冷刺骨。
通道的尽头,是一间全金属打造的、充满了科幻感的实验室。实验室里摆满了各种我看不懂的精密仪器,到处都是闪烁着指示灯的屏幕和密密麻麻的线缆。
在实验室的正中央,摆放着一个巨大的圆柱形玻璃容器。容器里,装满了某种像墨汁一样粘稠、漆黑的液体。那液体并不平静,表面在微微地蠕动着,时不时会鼓起一个气泡,然后又缓缓地破裂。
只是看着那团黑色的液体,我就感到一种发自内心的、源自生物本能的恐惧和厌恶。它不像刚才那个几何体一样直接攻击你的理智,但它散发出的那种纯粹的、冰冷的恶意,让我的汗毛都倒竖了起来。
阎王站在玻璃容器前,背对着我,声音幽幽地传来:“陈野,代号【疯子】。‘观渊’科目,你不仅撑下来了,还在最后阶段,尝试去寻找它的规律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?”
他转过身,那双黑洞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
“这意味着,你的精神构造,天生就适合干这个。也意味着,普通的训练,对你来说,已经没什么意义了。”
他指了指那个装着黑色液体的容器,嘴角再次勾起那抹冰冷的、令人不寒而栗的弧度。
“所以,欢迎来到你的专属小灶。你的下一个科目,是和‘它’,进行一次亲密接触。”
小说《我在异常收容部队服役的那些年》试读结束!
